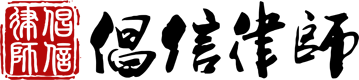未挂牌三轮电动车肇事致亡案:同等责任划分、保险全额赔付与被扶养人资格认定要点
2024年10月2日,张某驾驶一辆未悬挂车牌的三轮电动车,与包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包某的车辆失去控制,向左侧路边驶去,连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及行人任某发生碰撞,导致任某、张某受伤,以及多辆车辆损坏。张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不幸离世。经交警部门认定,包某与张某对此次事故负有同等责任。包某所驾驶的车辆在人保财险某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2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
由于事故涉及多车受损,交强险赔偿限额已全部使用完毕。张某的配偶李某及其子张某东、张某明共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包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20238.54元。
审理期间,被告人保财险某市分公司对李某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异议,辩称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身符合被扶养人条件。经法院深入调查核实,李某现年61周岁,持有三级听障残疾证,因听力障碍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且无任何固定经济收入来源。尽管李某与张某婚后育有两名子女,但经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及相关证人证言证实,李某的日常生活长期依赖张某的经济供养与生活照料。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的规定,结合残疾证、村委会证明等有效证据,依法认定李某属于法定被扶养人范畴。经严格核算,法院参照202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结合其他扶养人应承担的份额,最终判决支持李某19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核定金额为127642元(计算方式:20154元/年×19年÷3)。
经事故责任认定,张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需承担50%的责任。法院综合考量后,依法判决人保财险某市分公司向三原告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02989.29元。该案判决生效后,人保财险某市分公司已及时完成全部赔偿款的履行工作。
一、责任划分与保险赔付:“交强险先行 + 商业险按责分担” 的双重逻辑
交强险的法定赔付边界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交强险理赔规则,交强险实行 “有责必赔” 原则,无论被保险人责任比例如何,均需在限额内优先赔付。本案中,因事故涉及多车受损,交强险财产损失、医疗费用、死亡伤残三项限额已全部用尽,符合 “多主体损失共享交强险限额” 的实务处理原则,后续赔偿需转入商业险赔付阶段。
商业三者险的按责赔付核心
商业三者险遵循 “过错责任匹配赔偿比例” 的原则,同等责任下通常按 50% 比例分担损失。本案中,原告主张总损失 720238.54 元,扣除张某自身应承担的 50% 责任后,剩余部分由人保财险在 200 万元商业险限额内足额赔付,最终判决 702989.29 元,体现了 “保额充足时,商业险全额覆盖责任比例内损失” 的特点。需特别注意:若商业险保额不足,超出部分需由侵权人包某自行承担,但本案未涉及此情形。
二、被扶养人资格认定:夫妻扶养义务的司法实践突破
配偶成为被扶养人的三重要件
保险公司对李某被扶养人资格的异议,实质涉及《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夫妻相互扶养义务” 的落地适用。法院最终认定李某符合条件,需同时满足三项核心要件:
丧失劳动能力:61 周岁 + 三级听障残疾证构成 “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的直接证据;
无生活来源:无固定收入且未享受其他社会保障,排除 “隐性收入” 可能;
依赖受害人扶养:村委会证明与证人证言形成闭环,证实张某生前为主要供养人。
这一认定突破了 “被扶养人仅限未成年人或离退休人员” 的传统认知,明确夫妻间扶养义务可延伸至人身损害赔偿领域。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范式
本案计算方式 “20154 元 / 年 ×19 年 ÷3” 蕴含三重法律依据:
标准依据:参照 2023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154 元 / 年),符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 “按受诉法院上一年度消费性支出计算” 的规定;
年限依据:李某 61 周岁,按 “60 周岁以上每增一岁减一年” 规则核定 19 年,而非固定 20 年;
份额依据:两名子女与张某均为扶养人,故按 1/3 份额计算受害人应承担部分,避免重复赔付。
三、典型启示:受害人与保险公司的权益平衡要点
对受害人近亲属的举证指引
主张配偶被扶养人生活费时,需准备 “三位一体” 证据链:
身份证据(结婚证)证明婚姻关系;
能力证据(残疾证、劳动能力鉴定)证明丧失劳动能力;
生活证据(村委会证明、银行流水)证明依赖扶养。
对保险公司的理赔风控提示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异议虽未获支持,但提示其需强化两重审查:
审查被扶养人是否存在 “隐性扶养来源”(如子女实际支付赡养费);
核算多扶养人情形下的份额拆分,避免超限额赔付。
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
法院对夫妻扶养义务的认定,实质是将《民法典》的伦理精神转化为具体赔偿责任,既保障了丧失劳动能力配偶的生存权,也通过责任比例划分兼顾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