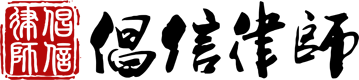骑车载同事体检出车祸,“好意同乘” 如何担责?
出于好心,骑车载同事去医院体检,不料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同事受伤,好心人该不该担责?责任范围又如何界定?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改判减轻了骑车人的部分赔偿责任。
黎阿伯与张阿姨同属某公司保洁员,且为同乡。由于某公司要求张阿姨尽快办理健康证,某日早晨,张阿姨在完成保洁工作后找黎阿伯帮忙,拜托他骑电动自行车带自己去医院体检。在两人均未向公司请假的情况下,黎阿伯出于同乡情谊,便骑车载张阿姨去医院,途中与吴女士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导致黎阿伯和张阿姨不同程度受伤,黎阿伯的电动自行车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黎阿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且违法载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吴女士承担次要责任,张阿姨无责。事故造成张阿姨腰椎、胸椎等多处骨折。
张阿姨认为,自己受伤是为了完成某公司办理健康证的要求,黎阿伯陪其到医院体检属于执行工作任务,应当由黎阿伯、某公司、吴女士和吴女士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未获赔偿,张阿姨将四方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保险人,首先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张阿姨损失,超出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 40% 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保险理赔范围及不属于保险理赔部分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应由黎阿伯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同时,一审法院驳回了张阿姨关于黎阿伯行为属职务行为、公司应担责的主张,认为黎阿伯陪同纯属个人情谊。
黎阿伯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上海一中院受理上诉后,将二审的争议焦点明确为:黎阿伯应否对张阿姨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范围如何界定。
本案中,黎阿伯驾驶电动车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和违法载人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具有明显过错,与张阿姨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黎阿伯作为侵权人应对张阿姨因交通事故所受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黎阿伯提出张阿姨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要求减免其赔偿责任。对此,上海一中院评析后认为,张阿姨在交通事故中虽经交警部门认定无责任,然其确实存在违规搭载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
同时,张阿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电动自行车不能搭乘成年人,但是她依然要求黎阿伯骑电动自行车带其去医院体检,可见其主观上缺乏安全意识,将自身置于一定的危险性中,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应对自身损失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综上,上海一中院依法予以改判,酌情降低了黎阿伯的赔偿比例,张阿姨自担了约 10% 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仍然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
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黎阿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并违法载人,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其过错明显,依法应对张阿姨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确定其责任范围时,必须考量受惠方张阿姨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黎阿伯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合理减轻其赔偿数额,避免对善意施惠者课以过重的责任负担,维护了社会互助的积极性。
本案中,黎阿伯出于同乡情谊搭载同事张阿姨就医,却因交通事故引发赔偿纠纷,二审法院改判减轻骑车人责任的裁判逻辑,背后蕴含着法律对 “善意施惠” 与 “过错责任” 的平衡考量。以下从法律依据、争议焦点、实务启示三方面展开解读。
一、法律依据:侵权责任与过失相抵的核心适用
1. 侵权责任的 “过错归责” 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黎阿伯 “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且违法载人” 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对交通安全的疏忽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张阿姨的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即使是出于好意的搭载行为,只要驾驶人存在交通违法或操作过错,仍需对损害后果担责,善意不能替代对安全义务的遵守。
2. 被侵权人过错可 “减轻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明确:“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这一 “过失相抵” 原则在本案中成为改判关键:
3. “好意同乘” 的特殊考量因素
虽然本案未直接援引 “好意同乘” 的专门条款(部分地区司法实践中对好意同乘有责任减轻的指导规则),但法院在裁判时隐含了对 “善意施惠” 行为的保护:黎阿伯搭载张阿姨是出于同乡情谊,无营利目的,属于社会互助行为。法律若对其课以过重责任,可能打击公众善意帮助他人的积极性。因此,二审法院在认定双方过错的基础上,酌情减轻黎阿伯的责任比例,既未纵容交通违法,也兼顾了社会伦理对 “善意” 的鼓励。
二、争议焦点解析:三大核心问题的法律判定
1. 黎阿伯的行为是否属于 “职务行为”?公司为何不担责?
张阿姨主张黎阿伯搭载其体检是 “执行工作任务”,但法院未予支持。判断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核心看是否 “基于用人单位授权或指示,且与工作内容相关”。本案中:
2. 交警认定张阿姨 “无责”,为何法院仍判其自担损失?
交警的 “无责” 认定是对事故发生的行政责任划分,侧重对交通违法行为的评价;而民事赔偿责任需综合双方对损害发生的 “过错程度”,不限于交通违法层面。本案中:
3. 责任比例如何划分?为何二审降低黎阿伯责任?
一审法院判黎阿伯承担 60% 责任,二审改判张阿姨自担 10%,核心逻辑是对 “过错程度” 的精细化认定:
三、实务启示:好意同乘需警惕三大法律风险
1. 驾驶人:善意施惠不能替代安全义务
2. 乘客:接受搭载≠免除自身注意义务
3. 责任认定:区分 “好意” 与 “过错”,平衡情理与法理
法律既保护受害人权益,也鼓励社会互助:对善意施惠者的过错责任,法院会结合其动机(无营利、纯帮忙)、过错程度综合判定,避免过重责任打击公众善意;但这一保护以 “驾驶人已尽基本安全义务” 为前提,严重违法(如闯红灯、醉驾)仍需承担主要责任。
结语
本案的核心启示是:好意同乘中,“善意” 不能豁免法律责任,但 “过错” 可以影响责任大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都需对自身行为的安全性负责 —— 驾驶人要严守交通规则,乘客要拒绝危险搭乘。法律通过 “过失相抵” 原则,既让过错方承担相应责任,也避免善意施惠者因一次意外承担过重后果,最终实现 “过错担责” 与 “鼓励互助” 的双重价值平衡。